期刊荐读 | 二战纪念仪式中的记忆传承与价值构建
作者介绍
李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从记忆传承、行为规训到价值构建,二战纪念仪式以历史“再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并通过行为规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价值认同。
本文为节选,点击此处查看全文。
记忆传承:二战纪念仪式中的认知记忆与习惯记忆
纪念之地,作为纪念仪式重要的象征符号,其意义构建的方法和途径更加复杂。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建造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造于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馆中的砾石、枯树、雕塑和万人坑遗址处处令人体会到当时的惨痛与绝望。纪念馆后经扩建,设计为“和平之舟”,正面像是一座船头,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向往;侧面像一把折断的日本军刀,象征着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空中俯瞰则是“铸剑为犁”的立面,表达了中国人民祈求和平的良好愿望。几种寓意的结合构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作为仪式象征符号的完整意象。

习惯记忆的产生有赖于身体实践。很多二战纪念仪式,都有集体默哀的环节,这是通过身体参与加强记忆的重要程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于每年的12月13日举行,这是南京沦陷纪念日,近万名各界代表胸戴白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举行仪式。上午10时,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时,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行人就地默哀。身体实践在纪念仪式中的程式化体现,对于形成长久而深刻的习惯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认知记忆与习惯记忆的共同作用下,记忆的传承才能具有持久力和穿透力。

行为规训:二战纪念仪式中的行为塑造与角色扮演
在纪念仪式中,无论是“他人在场”所形成的社会监督,还是集体关注所带来的情感连接,均在客观上促使个体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完成角色扮演。但真正促使个体进行按照社会规范完成角色扮演的核心内驱力是个体对自身实际状态的客观判断,在心理学上被称作“客观自我觉知”,即当人们的自我判断与社会所预期的状态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种焦虑,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人们或逃避,或通过努力降低这种差距。这种认识到差距,并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是个体进行角色扮演、寻求自我认同的内在动因。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规程包含集体默哀、敬献花圈等环节,还包含高唱国歌、宣读和平宣言,然后是领导人讲话、撞响和平钟、放飞和平鸽等。这些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规程不仅是仪式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参与者与死难者情感连接的桥梁和纽带。纪念仪式极具象征性的各种规程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在具体仪式规程的引导下,伴随着以自我认同为目标的自我评价,个体不仅行为会受到严格的约束,情绪的起伏、变化也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价值构建:二战纪念仪式的意义争夺与价值引领
与战争相关的纪念仪式必须给与正确的价值引领,这是毋容置疑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并不鲜见,缅怀死难者固然是战争纪念仪式的重要内容,纪念仪式对于构建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自豪感也至关重要,但这远远不够。战争纪念仪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立场反思战争,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所有人,无论国家、民族,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重要的是如何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反思战争,构建价值认同。
二战纪念仪式因其再现历史的特性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不仅对于人们记忆那段历史,还是塑造人们的个体行为,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认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战纪念仪式承载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包含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从记忆传承、行为规训到价值构建,二战纪念仪式以象征性地再现历史的方式向后人展示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这是所有“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本文载于我馆《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公众号将定期发布期刊最新目录、推介学术文章、介绍业内动态,公众号将成为广大研究同仁、史学爱好者的挚友和助手,欢迎关注!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诚邀赐稿。期刊约稿种类包括:研究论文、问题争鸣、史事考证、人物研究、图书评论、学术综述、口述历史等。来稿字数不限,并附有中文摘要(3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来稿请注明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工作单位、职称等)、研究项目名称及编号、通信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等。
联系电话:025-86898667
投稿邮箱:ppcpalm@126.com
联系地址:南京市水西门大街418号
邮编:210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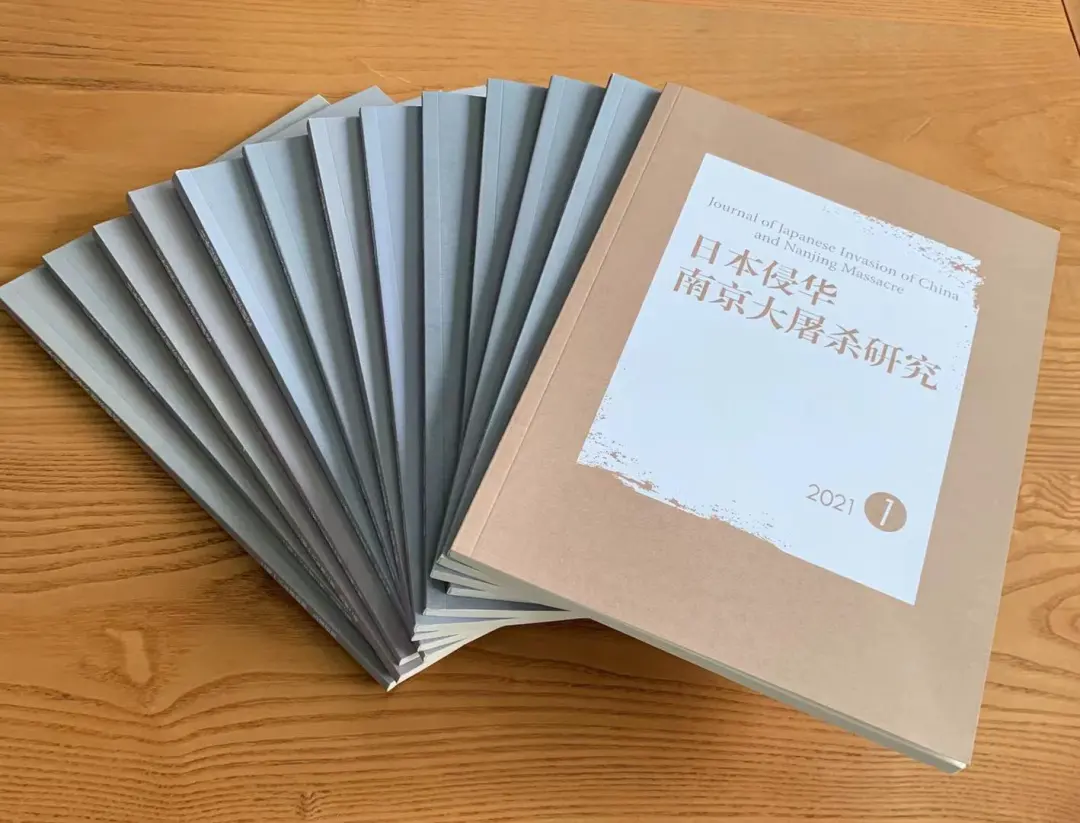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赵伊汉
监 制:凌 曦

